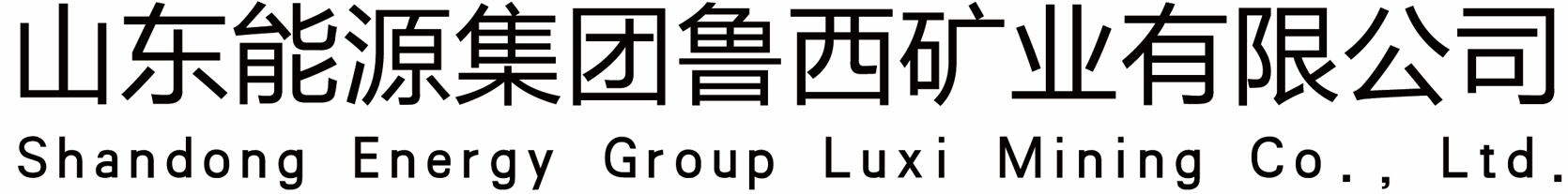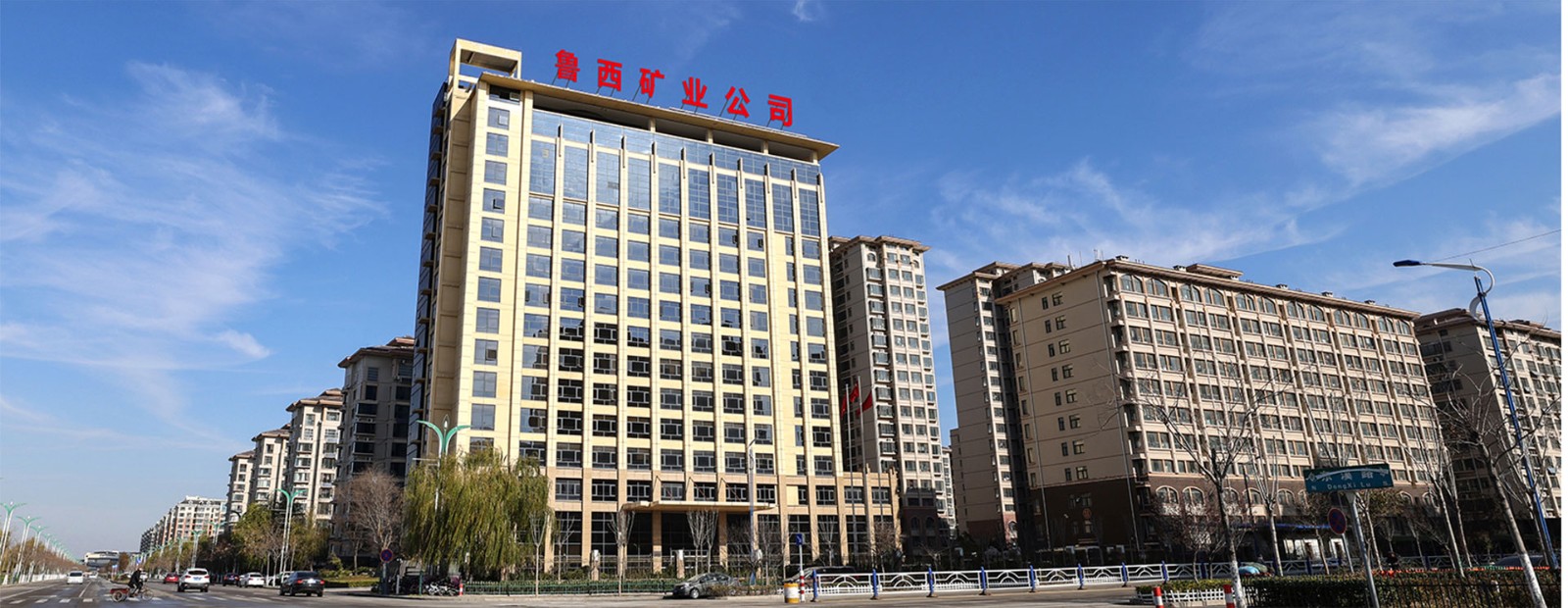谈起传家宝,别人家可能是金银珠宝,而我们家的传家宝却是姥爷留下的“千层底”布鞋。
我出生在沂蒙山那片红色的沃土,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就是听着《沂蒙山小调》和红嫂支前故事长大的。长大以后,才知道革命英雄就在我身边,那就是我的姥爷,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姥爷对千层底布鞋的不舍情感。
姥爷1925年出生于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山村下高湖村。他15岁那年,穿着老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离开了小山村,参军打鬼子、除汉奸。姥爷因为表现英勇也荣获了三等功,18岁就因表现优秀,火线入党。解放后,又投身于新中国人民公安事业,终身践行着“听党话、跟党走”的沂蒙精神。
小时候,我和父母乘坐绿皮火车从沂蒙山去美丽的西子湖畔看姥爷,母亲总会给姥爷带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母亲说那是姥爷最喜欢的礼物。我听母亲说,50年代,姥爷去北京开会,返程时路过家乡。走到村头,他脱下身上的公安制服以及脚上的皮鞋放在包里,换上普通的衣衫和千层底布鞋。后来我问起姥爷为什么这么做,姥爷说:“沂蒙山是我的根,走得再远,也不能忘本啊。回到沂蒙山,我就是村里的人,走在老家的路上,还是穿着布鞋得劲儿,自家的布鞋养脚。”
是啊,沂蒙山区山高沟深,无论是上山下地,还是布鞋最跟脚、最耐磨。行稳才能致远,脚下每一步路都要走好,才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做人也是一样,姥爷经常告诫我们是沂蒙人就要听党话、跟党走,要有革命老区人民踏实朴素、吃苦耐劳的样子,无论日子过得多好,也要秉承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姥爷自己的一生也始终保持革命人的质朴,家里陈设简陋,吃穿简单,尤其是千层底布鞋伴随了他的一生。他不允许在国家机关工作的舅舅乘坐公车回家,也不允许子女以他的名义谋取私利。他为母亲取乳名为“玉”,学名为“莲”,无不包含着他对子女们的期待:冰清玉洁、清廉一生。
在姥爷的影响下,我的母亲和身为普通矿工的父亲组建了家庭。父亲曾在五寺庄煤矿、褚墩煤矿、塘崖煤矿、株柏煤矿、古城煤矿等单位工作,虽然知道姥爷手中有一定的权力,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从未请托姥爷为他办过什么事,父亲说,作为亲人不能给姥爷添麻烦,父亲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奉献30多年。我自幼生活在矿工家庭,长大后成为一名“矿二代”,也像母亲一样和一名矿山人组建了家庭。2009年,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来光荣入党,成为一名纪检工作者。虽然没有像姥爷一样穿上军装保家卫国、穿上警服守护平安,却也坚守在纪检岗位上,为矿区的清风正气而忠诚履职。
2010年,姥爷重病期间留下“三不”遗言:一不要劳师动众举办追悼会;二不要舟车劳顿回家乡打扰乡亲;三不要占用国家土地资源,不搞土葬,骨灰撒入西湖。家人遵循姥爷的遗愿,将他的一抔忠骨撒入西湖的漾漾清波。姥爷的遗物里除了有军功章、离休证,还有一双磨损的千层底布鞋,成为我们的传家宝。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明媚的四月,母亲把一束鲜花摆放在西子湖畔。环顾西子湖畔,春风拂绿、绿水青山,满眼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姥爷虽然走了,但是他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却像传家宝一样代代传承,一直在激励和鞭策着我们,不忘本,不忘初心,听党的话,做好党的工作。耳边,春风飒飒,仿佛是姥爷又在用浓重的沂蒙山口音教导着我们:“要听党话,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