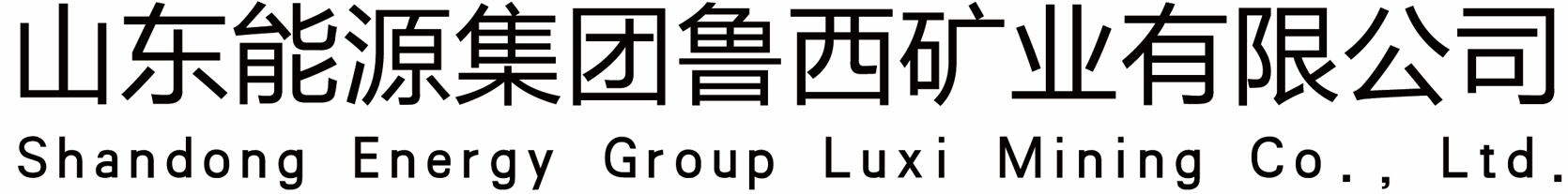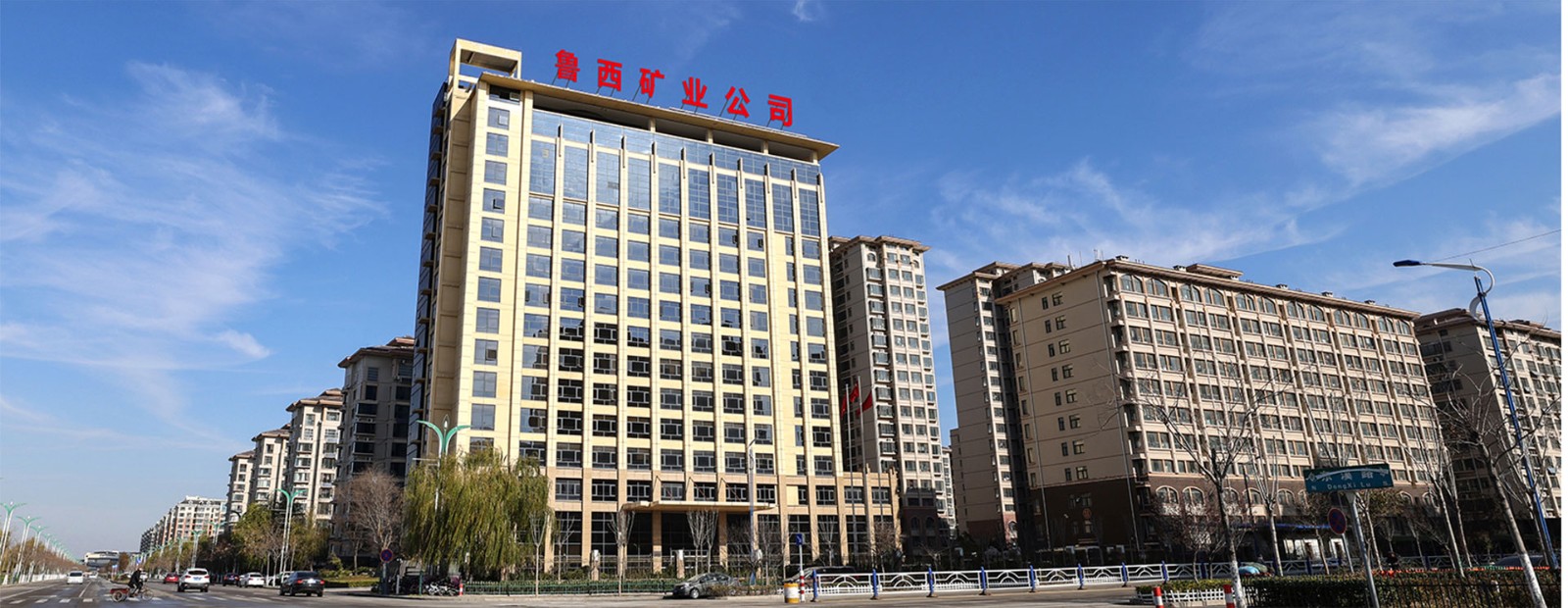在岁月的长河里,有一种声音,它轻柔却坚定,悠远而深沉,那是家风的低吟,于无声处绽放,于静好中传承。它,是家族血脉中流淌的智慧,是时间沉淀下的温柔,是每一颗心与心之间的默契与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说,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当我深入地思考、总结、复盘我的家风,哪有书香门第的文墨传扬,哪有氏族大家的著书立传,哪有家族宗祠的世袭传承,只是世纪之交一个农耕家庭默默无声的坚强拼争和日积月累和平凡坚守,细细品味,这种润物无声却成风化雨的点点滴滴,不正是护佑家人岁月静好的家风吗?
家风无声,岁月静好,家风就在父母的红砖房、承包地和奋力拼搏的生活中,它是一种自强不息。1978年我出生的当天,父母筹备、策划多年的5间红砖房正式打基开工,在亲朋友邻的帮助下,我们村的第一家红砖房落成,这是他俩从无到有、奋力拼搏的成果和骄傲,所以给我起名红方(谐音房),以表纪念。母亲说,分给家里的承包地是万万不可撂荒的,夏秋收成不好,也是会被乡亲们笑话的,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里年年“粮满仓”。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跟着母亲去乡里交公粮,她一路上最大的担心就是,不能让“公家人”收麦子时,一叉子下去验收不合格,还得求人说好话。有一年交公粮回来晚了,和同行的老乡到国道边上的“十里香”小饭馆喝了一碗面条,回来后常是唠叨,说口味不如自己做得好,埋怨自己多花了钱,这是我印象中母亲唯一一次下饭店。93年,母亲才42岁,他和父亲拿出大多数的积蓄,用2.8万元从县城购置了一套两层楼房的庭院,我们憧憬着要成为城里人了。那一年,家中诸事不顺,夏收后大旱,抢种的玉米也没有得到好的收成,秋季抢收时母亲感染了痢疾,耽误了医治溘然而逝。第二年,这些地,在我手里长了不少荒草,她要在世,一定会痛斥我。她短暂的一生,留给孩子们的是勤俭自强、奋斗不息的家风。
家风无声,岁月静好,家风就在姥爷的马车里、钉耙上和田间地头的劳作中,它是一种吃苦耐劳。姥爷的一生都在劳动、劳动再劳动,面朝黄土背朝天。他和姥娘共养育了8个儿女,在他们的带领下,舅舅、小姨们都是相互接济、互相照应、鼎力相助,勤俭持家,其乐融融。我上学的第一年,赶上母亲离世,家境困难,姥爷把苹果园的一年收成全给充了学费。姥爷当过生产队长,养过马、养过牛、养过骡子和毛驴,小时候坐在姥爷驾驶的马车里,多是讲积善行德向爱、励志求学举仕的故事,他一心想鼓励孩子们脱离农耕生活;每年秋收后,深耕翻地后需要耙地,这时候我和表弟常常轮流蹲在钉耙上作压耙的“石头”,跟在黄牛后潜移默化感受农耕文化;姥爷的西瓜地、苹果园都是我们儿时的乐园,跟着他观察农作物生长规律,蛇虫鼠的潜出时间,犁地、锄地、施肥、收获的农作经验,我们在表扬、赞许和激励声中得到茁壮成长。
家风无声,岁月静好,家风就在奶奶拾柴火、捡煤核和蹒跚着“三寸金莲”的岁月里,它是一种艰苦朴素。奶奶说,自从嫁给爷爷,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也向往着去县城这样的大城市开开眼界。上中专时我就许下愿望,等毕业参加工作,先带着奶奶去县城看看、逛逛公园、下个馆子,这一切之后都成了遗憾。小时候,每次来到奶奶的旧屋,饭屋里整齐地码放着她拾来的树枝和劈好的柴火,奶奶居住的小屋子桌底,堆积的是用旧砖作堰从砖窑或各家各户倒出的煤灰中捡回的煤核,这样奶奶基本不用买煤取暖。奶奶没有收入,94年我上学离家,她实在放心不下,硬塞给我30块钱,这该是她多少日子的积攒啊?也是她老人家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支出。寒冷的冬天,尤其是白雪皑皑,我在放学路上常拐弯到奶奶的小屋烤烤手、暖暖脚,就在这围炉旁,闻着煤炭燃烧的味道,依偎在老人身旁,听她讲家长里短、讲村里的故事、讲向上向善。
每年清明,细雨纷纷,思绪万千。当过往烟云一旦打开,长辈们劳作的点点滴滴皆属家风,父母们创造的一丝一缕皆含家教。他们虽然没有讲过仁义礼智信的操守、温良恭俭让的态度,忠孝忍勇廉的底线,却在质胜于华,行胜于言的无声无息中默默地践行和传承。
回忆我的家风,它更像大众文化,和风化雨,润物无声,它不像政治说教那么严肃,却比政治说教更有力量;回忆我的家风,它不像思想理论那么深刻,却比思想理论更能受用,它渗透了我的精神生活,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的价值取向。
家风,是岁月深处最温柔的呼唤,是静好时光中最坚实的依靠。它无声,却在每个人的心中回响;它静好,却在每个家庭的故事里熠熠生辉。